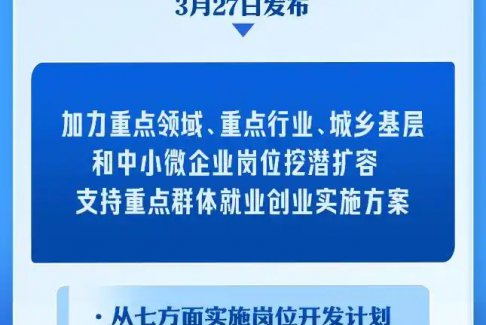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和损害一直是许多媒体报道即将于11月在埃及举行的Cop27气候谈判的核心。如果国际社会对气候受害者的声援不足,诉讼提供了一个重要但不完善的赔偿途径。
由于全球变暖和高温加剧了北半球的干旱,巴基斯坦的洪水“可能”变得更糟,气候变化已经在世界各地产生无法适应的严重影响的想法不再有争议。
但谁来为所有这些损失买单就不太确定了。
三十年来,最脆弱的国家一直在努力就损失和损害采取具体行动。早期的提议试图建立一个全球基金,最初被称为“保险”,各国将根据其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及其支付能力来支付费用(参见CarbonBrief的时间表)。
后来尝试使用补偿和责任的语言被证明是历史上排放量高的富裕国家的红线。专家将此部分归结为担心这会使各国面临巨大的法律和金融风险,从而为诉讼打开闸门。
2015年《巴黎协定》最终通过时,它承认通过华沙国际机制“避免、最小化和解决损失和损害”的重要性,但明确指出这“不涉及也不提供任何责任或赔偿的基础”.
去年在格拉斯哥举行的Cop26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富裕国家最终同意了损失和损害概念的框架,但并未就如何资助或谁应该为之做出贡献达成一致。
捐款的涓涓细流
9月,丹麦成为第一个为损失和损坏提供直接现金(1330万美元)的联合国成员国,苏格兰和比利时瓦隆地区也做出了类似的承诺。与气候脆弱论坛和V20国家计算的过去20年它们已经遭受的超过5000亿美元的损失和损害相比,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但希望此举会给其他富裕国家带来压力效仿。
然而,事实证明他们仍然非常沉默。人权律师HarpreetKaurPaul担心,早期的工业化企业将在Cop27上继续讨论损失和损害,“以信息和知识共享为中心——或不起作用的保险方法”。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的历史上,富裕国家逃避了在国内脱碳的责任,帮助其他国家也这样做,以及为调整和适应气候影响的措施提供资金,现在也越来越多地解决损失和损害问题,”她说。“他们拒绝参与损失和损害是那个困扰历史的延续。”
责任问题并没有消失。“我不能凭良心让加拿大纳税人承担可能无限的责任风险,”加拿大环境部长史蒂文吉尔博在5月告诉《国家观察报》。
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这个论点。在去年E&ENews的一篇文章中,法律专家怀疑仅仅在UNFCCC设立损失和损害基金会增加气候相关损害的责任。气候行动网络全球政治战略负责人HarjeetSingh直言不讳地说,富裕国家之所以有这种恐惧,“因为你知道你不会信守诺言,利用国际合作和团结来解决时间上的损失”。
欧盟最高气候特使弗兰斯·蒂默曼斯(FransTimmermans)承认,欧洲公民的支付意愿是有限的,“因为他们的担忧与他们自己在这场能源危机、这场粮食危机、这场通胀危机中的存在有关”。
诉讼的洪流
事实上,富裕国家所担心的诉讼闸门现在已经完全打开——这是国际不作为而非行动的结果。辛格说,损失已经上升到“人们将变得如此绝望以至于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上法庭”的程度。
气候诉讼在促使政府减少国家排放方面最为成功。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向历史污染者寻求赔偿。
早期向化石燃料公司寻求损害卡特里娜飓风和影响阿拉斯加沿海村庄基瓦利纳的海平面上升的案件失败了。秘鲁农民SaúlLucianoLliuya对德国能源公司RWE提起诉讼,他的家可能会被融化的冰川淹没,目前仍在激烈的斗争中,并可能为企业责任开创一个重要的先例。
小岛国成立了气候和国际法委员会。瓦努阿图正在争取国际法院就人权和气候变化发表咨询意见。LSE的格兰瑟姆研究所希望这些举措能够将这场辩论“超越迄今为止存在的主要理论领域”。
赔偿案件与损失和损害谈判的大部分内容相同,可以帮助弱势国家制定国际谈判战略。
它们给公司和金融机构带来了法律和金融风险。他们为气候危机的受害者发声。他们通过使用归因科学并阐明谁有法律责任支付费用,帮助解开有关因果关系的棘手问题——曾经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
谁应该得到赔偿?
然而,诉讼给更广泛的损失和损害谈判带来了一些风险。
首先,在法庭上败诉可能会传递更广泛的信息,即受害者在任何地方都不值得赔偿。
相反,成功的责任和赔偿诉讼可能会破坏UNFCCC的权威和合法性——尤其是华沙国际机制作为解决损失和损害的政治论坛——东芬兰大学法学院博士候选人PatrickToussaint认为。“从气候受害者的角度来看,这听起来尤其正确,”他在法律杂志Reciel中写道。
还有另一个问题。当美国开始对化石燃料公司提起诉讼时——这些案件现在已经到了管辖的关键点——一些人认为,赔偿不应该交给相对富裕的全球北方政府,而应该交给那些将首当其冲受到气候影响和最起码负担不起他们的费用。
“如果这些案例成为全球气候叙事的一部分,它们传达了什么信息,说明谁应该得到化石燃料公司和其他主要排放者的补偿和恢复?”KimBouwer博士在2020年发表于《跨国环境法》的论文中提出了这一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我仍然认为,”现任达勒姆法学院法学助理教授的鲍尔告诉TheWave。
她“对国际谈判没有产生任何资金或任何计划表示非常同情”。但是,尽管她认为如果秘鲁农民Lliuya赢得对RWE的诉讼,那将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损失的比例如此之小,不足以适当地减轻风险”。
一个“重要但不完美”的工具
保罗认为气候诉讼可以帮助制定规范,即气候损失和损害必须由那些不成比例地增加问题风险的人来补偿。
“但它是零碎的、昂贵的并且需要时间,”她争辩道。“提供公共赠款资金的多边机制有可能实现责任和公平,并且所有处于影响第一线的社区都可以使用。”
国际环境法中心气候和能源项目主任NikkiReisch将诉讼描述为“分配气候正义的重要但不完善的机制”。
她说,责任的前景为更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和为损失和损害提供资金增加了急需的压力,但“法院的大门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平等地进入的”。“这就是为什么法律行动需要伴随着对系统性变革、政策措施和协商解决方案的倡导,以确保更深远和公平的补救措施。”
一个名为“系统正义”的新非政府组织试图从根本上改变法律对争取种族、社会和经济正义的社区的运作方式,但遭到了更强烈的批评。它将更广泛的气候诉讼运动描述为由“白人、中产阶级和健全的观点”主导,并表示可以建立更多的案例来解决气候危机造成的不公正现象。
尽管它们有相似的目标,但气候诉讼和政策谈判的孤立世界之间几乎没有重叠。Toussaint发现“这两个领域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并指出他分析的所有损失和损害诉讼都没有涉及UNFCCC的华沙国际机制。
“对于索赔人来说,参考UNFCCC关于该主题的工作的唯一好处是支持这样一种论点,即目前的国际政策反应严重不足以保护那些受到伤害的人,”他总结道。
生活经历
Toussaint看到了参与气候诉讼和政策的各方可以更好地合作的几种方式,包括有针对性的非政府组织宣传、支持弱势国家代表团将诉讼作为谈判策略,以及提高专家气候律师贡献的诉讼网络(例如由Urgenda设立)。
与此同时,保罗要求战略诉讼当事人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说明气候变化如何损害住房、土地、生计、水、健康和医疗保健、教育等等。尤其是岛民提起的诉讼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Singh对诉讼律师的呼吁是最终指向UNFCCC下的全球机制。“想象一下,你将一个国家告上法庭,法庭说你必须为损失买单,但随后他们决定付给谁。我相信通过一个公平公正的系统付款会非常有帮助。”
但即使是国际协议也不太可能意味着诉讼的结束。Toussaint,现在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的副专家,他在论文中写道,即使要在国际层面商定新的损失和损害资金,“关于资金如何分配和获取的问题仍然存在当地受影响的社区”。
他说,如果人们认为国际商定的资金没有得到适当分配,或者在无法用现金轻易弥补的非经济损失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仍会提起诉讼。
脆弱的国家从不希望事情变得如此好斗。Singh认为气候诉讼是一种有用的工具,可用于向污染者施压以解决损失和损害问题,但实际上更希望人们的能源投入更具建设性。“我们想要一种合作的方式,”他叹了口气。
本文“”来源:http://www.wenzhou.co/qihoubianhua/2592.html,转载必须保留网址。